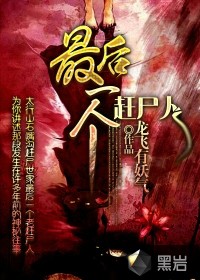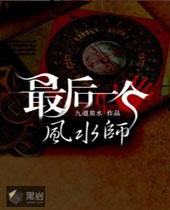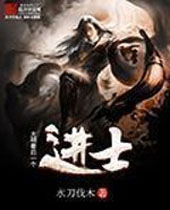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个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下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他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共产党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
我只是哀叹,一个教师教了十几年书,他的学生已有不少人也当起教师,可他自己还不能是一位“正式”的教师。好的是学生没有瞧不起我。就在我为此东奔西走的时候,一位过去在崖崎小学读书的学生,特地跑到家里来找我。他刚说已来了三次才见到我。我感到一点宽慰,难得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看得起我。他已是成人,第一次跟一位长大了的学生谈话,觉得师生感情依然存在。虽然我的处境十分狼狈,他却照样在尊敬和爱戴,视我为他的一位难得的启蒙老师。其实那时已经不是我去指导他们,而该是他们来给我指点和帮助了。但看得出他仍对我抱着“个人迷信”。也许我过去的确做过一些对学生有益的事,我自己是完全不记得。他那样地敬重,我倒要后悔当初做得太少。可想着眼下不应有的待遇,我又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
社会就这样地不公平,因为受过“审查”就不得“转正”,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后来据有关人员透露,早在1962年组织上已对我的问题作出如下结论:“经公安机关侦查,纯属集邮活动,没有政治目的、企图和活动,其团籍和就业问题应给予解决,此案不必复查。”可是“清队”中一些人总想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引诱我写出假口供,然后据此要定我的罪。后来出自某些人卑鄙的目的,竟然将1962年的“结论”抽掉,将我写的“翻案声明”毁掉,企图造成一条“悬案”来掩盖当初的“错案”。那时又没有人愿意替我来解开这条“悬案”,就这样将我“挂”着,就这样不得“转正”,就这样只能领取菲薄的薪水。我着实感到愤愤不平。
“转正”一事毫无结果,1973年家庭在农村“插队落户”又遇到麻烦。乡下的干部、群众对居民“上山下乡”越来越不满,认为这些人到农村占用了他们的口粮,而政府答应减少统购的诺言又没有兑现,于是迁怒到“上山下乡”居民身上。对他们百般挑剔和歧视,制造事端,追讨住房,不发口粮。许多“插队落户”的居民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只好“倒流”回城里来。这种情况各地相互效仿蔓延,我们的遭遇也不例外。房东开始索要房子,而且态度十分蛮横粗暴,声称限期不搬,就要拆除门窗。我找他们评理,他们觉得可笑,讲政策,他们说我是“书呆子”。美娟一人应付不了,只好搬回城里住。这一来成了“黑人黑户”,要吃“黑市粮”。以我每月二十几块薪金怎么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往后的日子又不堪设想。
搬回城里后,起初美娟每天照样走十几里路到乡下去出工,希望还能分到口粮。可是麦子入仓了,稻子收割了,仍是一粒粮食也不分给我们。美娟只好死了这条心,开始在城里找活干。刺绣、裁缝、雕刻、泥匠小工,只要有活就去干。甚至一度替人挑粪尿,一天五角钱。有一次体力不支跌倒在地,溅了一身臭。她爬起来,回家洗一洗,换件衣服,照样又去干。邻居好友十分同情,但同情不能当饭吃。后来她又到大街上摆小摊,贩卖零食。我因成了“堂堂教师”,不大愿意她出去“抛头露脸”,有碍“声誉”。可除此外,别无法子可想。她原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妻子,生活把她折磨得有点衰老。她把全盘的思想都倾注在求生上,倒是我不时阻拦着,妨碍她这种欲望的尽情发挥。我甚至怪她埋头于求生而忘了生存的另一含义。可是我的见解是错的,她为生活勇挑重担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她不愧是我生活中亲密的朋友和患难与共的伴侣。
那时两个孩子也相依为命度过他们苦难的童年。早在乡下,姐弟俩没有保姆,没有玩具,留在家里只有孤单和哭泣。小儿不会走路,只好关在房里,任其哭闹,直到声嘶力竭,感到无望为止。小女跟随邻居的孩子上山捡树叶,有时在家见弟弟饿了,也会动手把锅里的饭温热,喂上弟弟几口。我虽然觉得艰难的环境,也许可以养成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愉快?逢年过节我便带他们回城里,让他们熟悉自己的老家和这里的亲人。这是“根”的所在,谁愿意背井离乡寄人篱下?每次一路上姐弟俩都会欢天喜地。小女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边哼着自己编的曲子,那歌曲虽无章理,却十分悦耳动听,让父母听着心里快活。小儿总是不眨眼地望着陌生的世界,象一位小画家,正在构思一部伟大的作品。大约天下做父母的总对自己的孩子有点偏爱,无论自己的孩子怎样蠢笨,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可喜的变化,觉得他们一点小小的进步都是惊人的成绩。正如再糟糕的孩子照片,也能让父母找到可爱的痕迹一样。看着他们,我心中的不平和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感到世界本该是美好的。
“倒流”城里后,两个孩子更可怜了。一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从学校回来,看到他们还在外面奔跑,小女光着上身,小儿流着鼻涕。姐弟俩见到我象看到救星一般欢呼雀跃,边喊“爸爸”边冲过来。我知道美娟又出去摆摊子,留下两个孩子成了流浪儿。我又是心疼又是难过,然而我还不能马上抱起他们,我得赶去问问黄组长,“转正”一事怎样了,还有“上山下乡”“回收”的事也要去打听打听。我放下自行车,顾不得孩子早已盼望的心情,立即又跑出来。可得来的仍是失望的信息。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却不见了,又到外面去等他们的妈妈回来。我呼叫着,小女在公路边应答,小儿吧哒吧哒跑过来。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两个孩子跟我们一样在受罪呀!
进到屋里,我赶紧动手做饭,姐弟俩乖乖地在一旁等着,只有小儿细声说:“爸爸,我肚子饿。”偏偏柴草不干,烧着了又熄了,冒出股股浓烟,急得我满头大汗。幸亏这时美娟回来,放下担子就过来帮我烧火。两个孩子却伏在椅子上睡着了,只得把他们抱到床上去,可刚一放下又都醒过来。好容易煮好饭,已是晚上九点多,这时祖母过来“告状”:“早上那小的爬到楼台的栏杆上,太危险了。”美娟一听就骂小女没照管好弟弟。小女委屈地哭了。我心里很难过,应该怪我们没能照顾好他们。美娟不理解我的心情,埋怨我纵容了孩子。我知道那些日子美娟够苦的,一大早得起来做饭,然后到集市上买生花生,回来得赶紧煮熟再挑到街上去卖。晚上要料理家务,给孩子洗澡换洗衣服。我看她瘦了许多,不禁又叫她别去排摊子。她十分生气;“我又不是喜欢这样,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可不这样又怎么办?一斤黑市米四角多钱,你每月的薪金光买三个人的口粮还不够呢?”是呀!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逢上星期天,我在家里尽量多做些事,支援美娟“做生意”。替她煮花生,再让小女送到街上去。有时小女提不动,我就亲自去送,小儿哭着要跟上,三人只好结伴向大街走去。这时我仿佛觉得人们在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便不屈地昂起头来,在苦涩中显露高傲,正视这真正的人生。就连小儿也会为这种贫困感到“自豪”。那时他不得不穿着姐姐退下来的旧衣裳,邻居小朋友便笑话他,可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件衣服我有,可惜你还没有呢!”他一点不为自己“男扮女装”感到羞愧。这种“自豪”恐怕也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有。来到街上。美娟正寂寞地蹲在街旁叫卖,看见我们,象是得到极大的鼓舞,我想她心里一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患难中最需要相互支持。大凡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园,不要把那些生活穷困,灾难深重的人看得过于悲观,就连在路边行乞的人,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美娟告诉我,前几天小儿竟独自一人跑到大街上。当他找到妈妈时,又蹦又跳,嘴里不停地欢呼他的胜利,这是他来到这世界第一次独自走出家门去找妈妈,他能不高兴吗?可我们都吓得要命,多危险呀!小儿毕竟还不满三岁。
星期一我必须回学校上课。美娟照样一大早就出去,照看小儿的任务还是落在小女身上。她总是懂事地点着头,小声“嗯”一声表示同意,可语调嘶哑,眼角边似乎还噙着泪花。有时小儿哭了,我只好等他不注意时悄悄溜出去。而小女却叫起来,声音有点凄厉,尽管她答应过,可看到爸爸离开,妈妈又不在,她能不感到孤单害怕吗?她才刚刚五岁。结果小儿也哭了,此时我怎能忍心走开,只得回来哄骗他们。最后没办法,也只好让他们去哭了。我想只要不出危险不生病,苦是一种锻炼,对孩子的将来有益。我不为此感到悲哀,看到别人的孩子穿着漂亮的衣裳在嬉笑,我一点不羡慕,只有无所忧虑的人才会满足这种幸福。我认为人的一生,不在童年的遭遇,童年是短暂的,孩子也是无所烦恼的,决定的是成年之后,走进社会面前是一条怎样的路。我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翅膀长得硬不硬,能不能高飞翱翔,冲破云层去异国他乡观光觅食。倘若只知道在原地打转,再肥胖也只是一只庸鸟。
居民“上山下乡”政策的失败,造成许多“黑”人“黑”户在城里到处游荡。这些人络驿不绝地扣打当年负责“上山下乡”事务的“四向办”大门,愤怒围追县革委会要人,要求返回城里居住。但是那些当官的,办事的,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他们也做不了主。拿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请功有人干,一到谈“回收”,是纠正工作过错,等于打自己的嘴巴,就谁也不愿做了。
有一次我到“四向办”去想反映一下自己的困难情况。一位年轻干部摆出一付官架子,对人不屑一顾。我站在一旁也冷冷地看他怎样对愁眉苦脸的群众高声斥责,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