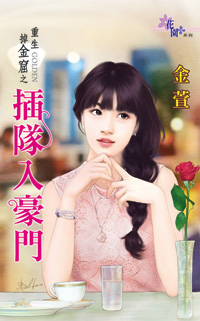插队在黄土高坡-第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婿,生了娃不姓李,莫非还姓薛,白纸黑字写着呢。”
二红哥李大宝说:“爸,人家对咱家不赖,又出钱,又出血的,咱不能这么绝情,这娃,其实种也是人家薛家的,姓薛姓李不都是二红的娃吗?”
“你个狗日的,你让咱家绝啊,你没本事娶媳妇,养老女婿生了娃,不是咱家的,莫非生生给人家?”
大宝见父亲骂他,也生气了:“我没本事娶媳妇,怪我啊,怪你和我爷是地主,你们要不是地主,我能娶不上媳妇这年头,谁敢嫁黑五类的地主儿子呀?”
“你哥狗日的,看我揍你!”大宝爸脱下鞋举起要打大宝。
“你打!你打!”大宝不但不跑,反而顶着父亲举着的鞋,梗着脖子低头迎上来。
“别打了,别打了!”大宝妈哭着腔哀求道:“人家批咱,斗咱,欺负咱,就够了,咱自己还打起来,成甚了,你爸你爷是地主,他们不好,可你也不能老拿这埋怨呀!”
第七十五章 起名
“不埋怨他埋怨谁,地主就是那么狠,那么贪心,刚见人生了俩娃,就想占为己有!”大宝仍是气嚷嚷的。
“要不这样,这俩娃,一家一个,反正都是男娃,一个姓李,一个姓薛咋样?”大宝妈说。
“也行。”大宝爸想了想,点了下头,把举了半天的鞋放到地下。
“什么?你说生的孩子一个姓薛,一个姓李,一个算薛家孙子,一个归李家?”薛玉昌的母亲听完亲家爸讲的这句话后,立刻惊呆了。
“我是说,养的两个男娃,你家没孙,你要一个,我家也没孙,我家也要一个,这样薛家,李家都有后了,不是两家都好吗?”二红爸在堂屋里叼着长杆烟袋说。
()免费电子书下载
“可是,如果今后哪天玉昌又调回北京,二红和娃们要随他回北京的,留一个姓李,不姓薛,到时候怎么跟他回京啊?”薛玉昌的母亲想了想说。
“玉昌还能回北京?”二红爸虽然常琢磨这事,可是听亲家母亲亲口说,不觉得心里还是一震。
“他本来就是北京孩子,说不准哪天政策又允许回去呢?”薛玉昌母亲解释道。
“哪一天啊?”二红爸追问。
“我只是这么想,也许三五年后,也许一二十年,也许一辈子都回不了北京,在这扎根开花散叶了”
“噢,您是说没准,也就是回北京还没准谱,回北京只是您想的,那我跟你掏心窝自说句话,我儿啊,都三十多岁了,也没娶上个婆姨,您知道,家庭成分不好,地主。说是地主,解放前也就几十亩地,雇了俩长工,也没甚钱,解放了,又抄家又分田分地的,更没甚钱了,儿子扣着个出身地主的帽子,又没甚钱,一直没娶上婆姨,今后更难了,恐怕一辈子要打光棍,我家再穷也不愿断了烟火,所以,就招玉昌当养老女婿,为的是能给我家留个后”
“什么,玉昌是给你家当养老女婿?”玉昌妈听此话,大感意外,惊得立马站了起来。
“是,他写了字据的。”
“还写了字据?”
“我拿给您看。”二红爸转身进了里屋,拿字据去了。
“玉昌,你真行,娶个农村媳妇就可以的了,怎么还当了人家养老女婿?”玉昌妈把玉昌从东屋叫到院里,低声问。
“是啊。”玉昌一点也不感到慌乱,好像早预料到母亲要问他这句话一样,平静地说。
“为什么?”
“因为春节,别的知青都回北京的家了,我回哪啊,我吃没吃的,喝没喝的,人家二红对我好,我怎么不能和他结婚啊?”薛玉昌话语仍然很平静。
“结婚就结婚呗,为甚非要当养老女婿?”
“妈啊,您说话不腰疼,结婚得要钱啊,我身上只有两块钱,人家结婚光彩礼就要二三百,又要新衣服,新铺盖,又要房子,我哪里去弄啊”
“那你不会先不结婚?”
“先不结婚,肚子一天天变大,再不结,就显形了。二红本来就是地主子女,在村里抬不起头,如果再挺个大肚子没主,那不成地主加破鞋了,我不能害人家啊”
薛玉昌妈沉思起来,良久才说:“二红爸要把娃留一个给他李家,你说咋办?”
薛玉昌笑了,说:“那就给他留一个姓李,另一个姓薛,我这几天一直琢磨她爸是不是想让两个娃都姓李呢。”
“你怎么不当回事?”薛玉昌母亲见儿子这样,不禁有些生气。
“这有甚啊,当初说的就是给人家当养老女婿,生了男娃要姓李,现在给你留一个,不错了。”
“我可舍不得,哪天你要调回北京,那个娃不姓薛,咋调啊?”
“回北京,驴年马月吧!”薛玉昌淡淡的说。
“她哥为什么娶不上媳妇,我看她哥人长的也不错,也挺棒的,是不是因为地主成分?”
“我说啊,前两年文化革命,主要是地主成分影响的,你整天让人批斗,谁都敢抓你,捆你,给你戴高帽子,游斗,哪个姑娘敢嫁你,不也被人欺负,游斗啊。这才过去两三年了,村里又不像城里那么继续搞文化革命,现在,成分不是主要的,是没钱,没钱咋娶媳妇?”
“他娶媳妇要多少钱?”
“别的都好说,彩礼钱怎么也得二三百。”
“怎么那么贵?”
“成分不好,年岁又大,人家姑娘不得多要钱?”
()
“玉昌,妈跟你说,妈这还剩二百快钱,刨去路费,我还能给你们一百五六十元,本想留给你和孙子们,可是,人家待咱不赖,咱就把这一百五六十元给二红他爸吧,请二红爸让两孙子都姓薛好不好?”
薛玉昌望望母亲恳求的目光,说:“我去跟二红爸商量商量。”
二红爸一百五十元拿到手,果然不再坚持要一个孙子姓李了,薛玉昌的母亲说:“趁我在,给俩娃取个名字吧。”于是两家人开动脑筋给娃起开了名。
二红妈说:“给娃取名,大的叫大狗,二的叫二狗,贱名好养活,娃不容易生病。”
二红爸说:“不行,娃他爸是北京人,哪能给娃取名叫大狗二狗呢,本来文化革命管咱黑五类的子女就侮辱叫狗崽子,你生了孙,再管他叫大狗二狗,那不承认自个成了狗崽子么?”
“那叫甚啊?”
二红爸说:“不是说咱成分不好吗?咱给娃取个革命的名,一个叫薛心红,一个叫薛红心。”
二红妈忙说:“不行,娘叫二红,儿又叫心红,重了字了。”
“重字怕甚,和爹重字不行,和妈重字没甚事!”二红爸自鸣得意地说。
薛玉昌听着丈人和丈母娘说出的名,觉得都不太好听,于是望望自己的母亲,希望母亲给这两个孙子起个名,薛玉昌的母亲想了想说:“我想孙子生在山西,父亲又是北京人,干脆老大叫薛晋京,老二叫薛京晋。”
“甚,叫进京,进北京啊,当然好。”二红妈当下听了这名,觉得兆头好,便首先同意。
二红父亲见老伴同意了,又是亲家起的名,觉得名也不错,说对了,没准真能自己的闺女和两个外孙都能到北京呢,那是自己也到北京逛逛,瞧瞧**,于是啧啧称道:“这名好,这名好,就叫进京和京进吧。”
“你找谁啊?”薛玉昌母亲推开院门,便见村里那来过家里的媒婆领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站在门外。
“你是,你是玉昌妈吧?”那媒婆笑容可掬地先开了口。
“她是?”薛玉昌母亲瞅了那三十来岁的妇女问。
“这是给大宝介绍的对象,是定襄桃树村的。”
“大宝相的对象请进!”薛玉昌妈忙把三人让进院子。
二人进了院子,薛玉昌母亲才发现,这三十来岁的妇女,虽然长的还行,白白净净大圆脸,可是一走路,怎么风摆荷叶两边倒啊,原来是个拐子。
“大宝妈,我把对象领来了!”没进屋,媒婆高声大嗓地喊了两声。
屋里大宝爸,大宝妈,大宝,忙迎了出来。“进屋,进屋。”大宝妈忙招呼。
可是那妇女并没忙进屋,而是在院里瞅了瞅一排五间正房,又瞅了瞅东房,西房,还问媒婆,“刚给开门的是谁?”
“是女婿的妈,在北京是个大干部,儿媳生娃,特意从北京来山西看儿媳的。”这时,这妇女脸才露出笑意,随众人进了屋。
相亲,就是女方来男方家里考察男方家里的房,家具,财力如何。再看看男方家里的人,对象怎么样,,是不是全须全尾,个头长相,年岁,是否痴呆,口气,缺胳膊腿短,要和媒婆讲的差不多,才能定亲。
李家客客气气地招待一通,送走这妇女后,媒婆又回来了,说:“女方挺满意的,如果男方同意,过两天就定亲。”
“她多大了?”薛玉昌母亲插话问。
“三十五。”媒婆说。
“比大宝大吧?”
“大三岁。”大宝母亲说。
“我看她脚拐。”薛玉昌母亲又说。
“是拐点,可不敢耽误养娃。”媒婆答。
()免费电子书下载
“三十五了,没嫁过人?”
“嫁过,爱人进了城了,把她甩了。”
“有娃吗?”
“有俩娃,男娃他爱人带走了,女娃留给她,她也是没法了,养不起女娃了,才嫁咱家”对薛玉昌母亲一连串的问,媒婆爽快地一连串答,不遮不掩,十分利落。
“脚又有点毛病,又带个娃,大宝寻她是不是吃亏了?”薛玉昌母亲瞅瞅大宝问。
“不赖,比想的好,像咱这成分,能娶个婆姨就行。”大宝还挺满足。
“还带着个娃呢?”薛玉昌母亲说。
“带个娃怕甚,咱就喜欢女娃,她过来,再养个男娃,不是有儿有女了吗?”大宝笑着说。
天气渐凉,收割正忙。知青们和村里人一样,都忙着到大田里收割去了。
第七十六章 收获
下李村秋收主要有三大庄稼。(pm)玉米,高粱和棉花。当地人管玉米叫玉茭子,管高粱叫高粱茭子。妇女们都兜着个大布兜子,到棉花地里采棉花。女知青也都去了,这里棉花长的不太高,而且采棉早十天半日就开始了。采棉也不过秤,一人一垅往前采,把张开棉桃的棉花捏出来,没张开或只张开一个小口的棉桃留下,过几天再采,所以采棉花的妇女除了弯腰有些累外,倒也说说笑笑,不觉劳累。
掰玉米的社员和男知青就没采棉花的妇女轻松了,一人两垅,把长在棵子上的玉米棒子都要掰下来,除了没长粒的蔫棒子外,大凡长粒的都要掰下。初时,男知青挎着个筐,和村里社员一样,掰了一筐,倒到地头的马车驴车上,几个来回下来,没有手套的手便磨的生疼,外指中关节上还大都磨出水泡。太阳又照,干玉米叶子又划,脸上脖上都划的一道道的,流出的咸的汗一浸,生疼搔痒,烦心的难受。可是看人家掰棒子的男社员,一条毛巾往脖子上一扎,一个烂草帽脑顶一扣,掰棒子,倒也三两个人相伴着,嘻嘻哈哈的谈笑,没见他们什么苦和累。
“真操蛋的,咱怎么就没带个草帽和扎条毛巾呢?”金阳边掰棒子边对隔的不远的单丁一说。
“毛巾倒有,可草帽,早不知扔哪了。”单丁一接下话茬。
收割高粱不是从根上割,而是只割高粱穗。下李村钟的高粱,除了种了十来亩高杆的高粱,收割后编扫帚外,其余钟的都是只有齐人高的杂交高粱。杂交高粱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