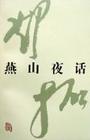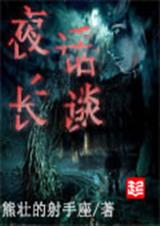燕山夜话-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写了真实姓名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作者?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片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历来许许多多严肃认真的作者,他们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中国古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有别号或笔名。例如,唐代的诗人杜荀鹤,有时署名为九华山人;宋代的文人黄庭坚,有时署名为八桂老人;元曲大作家关汉卿,有时署名为己斋叟;明代大学者王夫之,有时署名为一飘道人,时至今日,人所共知的鲁迅、茅盾、老舍等等都是笔名,他们岂不都是严肃认真的作者吗?可见一个作者的态度是不是严肃认真,与他们用不用笔名简直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有人会说,过去那许多作者使用笔名,都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经常威胁着许多进步作者的生存。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之下,许多作者使用笔名是情有可原的。现时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再也不受什么威胁和迫害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用笔名来写文章,而不写真实姓名呢?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也不然。笔名的作用是颇为复杂而微妙的。著名的《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偏偏不用真实姓名,而用了“蘅塘退士”的笔名,谁能解释其原因何在呢?假如说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情可以不论,那末,即便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优越的社会制度,仍然没有完全取消笔名的理由。正如现在人们虽然都知道茅盾便是沈雁冰、老舍便舒予,如此等等,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取消茅盾、老舍等笔名,而无论在任何和任何场合,都一律只用沈雁冰、舒舍予等本来的姓名。
如果这些著名作家的笔名和本来姓名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不管用的是什么名字都是完全负责的;那末,现在许多新的作者使用笔名或真实姓名,不也是一样都要负责任的吗?
现在的新作者发表文章的时候,几乎无例外地都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了报刊的编辑部。这就是说,无论署什么名字,作者都是负责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有的同志更加坚持己见,认为使用笔名已经毫无意义了。殊不知在现时条件之下,使用笔名还是有若干正当理由的。
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这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初步心得,但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既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会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读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
由此可见,写文章用笔名的,只要作者完全负责,就决无坏处,反而有好处。那末,请问你赞成用笔名吗?
编余题记
这一集又选了三十篇,重复编校,现在付印了。
在前三集出版以后,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据说,外地报刊有的转载了《夜话》的某几篇;也有的只采用了其中若干主要的材料,另行编写,而未转载原文。这些读者都热情地把剪报寄来,使我直接了解到更多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对于改进《夜话》的内容很有帮助。
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这固然是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但是,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特别是当别的作者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都不应该把不同的意见,“顶回去”,而应该让读者有机会充分地研究不同的意见,做出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辨驳呢?这种态度你以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这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问题。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即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的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还有一些读者大概没有看到《夜话》已发表的全部文章,他们来信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讲过了,恕我不再重复。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共通的门径
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窍门没有?这是朋友们在谈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记得有一次《夜话》的题目是《不要秘诀的秘诀》,中心意思是劝告大家不要听信什么“读书秘诀”之类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的这个意见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近来仍然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多讲些学习方法。他们说:“不一定要什么秘诀,指出一点门径就好。”为了答复这个要求,现在另外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有的读者也许以为我喜欢看古书,所以来信要我“开列几本古书,作为学习的入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不主张大家以古书为入门。古书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读的,否则越读越要糊涂。而且即便有了一定条件能读古书,也不可陷在古书堆里拔不出来。
明代有一位学者曹于汴,在他所著的《共发编》中就曾经说过:“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这个见解很对。曹于汴的为人处事,也正表现了他的这种独立不阿的精神。他在明代万历年间举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力持正义,终为魏忠贤那一伙奸臣所不容,那是必然的。
当然,这样的读书态度并不只曹于汴一人。从来有学问的人都懂得:“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于盲目地靠读古书,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
如果一个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就很难谈到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等等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不能设想,一个文字不通的人,怎么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能够通晓各科知识呢?
如果一个人连一般的逻辑都不懂得,当然就很难进行正确的思维,很难对自己接触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概括,更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了。事实证明,有的人正是因为缺乏逻辑的基本训练,常常说了许多不合逻辑的十分荒谬的话,自己还不觉得它的荒谬,甚至于还自鸣得意。也有的人因为不懂得逻辑,对于别人不合逻辑的荒谬言论,竟然也不能觉察它的荒谬,甚至于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自己要研究什么学问的话,最好想想自己是否学会了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如果不会,就必须先把语言文字和逻辑常识学会,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学会以后,还要不断地练习,越练越熟,当然就越善于读书,越会做研究工作。没有练好基本功以前,并不是完全不能做专门的学问,只是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是,也不必等到基本功完全练好了,然后才去做专门的学问,尽可以同时并进,双管齐下。
当着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基本功,能够独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找到自己要研究的专门问题的书籍,抓住适合自己需要的最重要的著作,哪怕只有一两本也行,把它读得烂熟。透彻地理解它的全部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无妨广泛地阅读其他书籍和参考资料,越多越好。这样日久天长,自己的知识必然会丰富起来,再加上实际调查研究和亲身实践的体验,就不难在某一专门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一点半点的成绩来。
有的朋友在来信中还再三谈到博与专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表示很苦恼。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博与专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无所不知的博学之士,也没有只知一事一物而不知其他的专门家。同时,在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之内,仍然有博与不博、专与不专,也就是广与不广、精与不精之分。一般说来,在博的基础上求专,或者在专的基础上求博;先求博而后求专,或者先求专而后求博,都是可以的。
在练习基本功和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时候,书要一本一本地精读。正如明代胡居仁的《丽泽常学约》上写的:“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勿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打好了基础之后,为了扩大知识的领域,就要多读多看,如汉代王充那样,“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才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
无论如何,每个人的情形不同,水平不同,要求不同,上面说的这些当然不能完全适合于每一个人。这里只不过提出一个共通的门径而已。
主观和虚心
平常说话、做事、写文章,往往发现有主观片面的地方,心里就很后悔,同时也很快就会受到朋友的批评。但是,这种主观片面的毛病,又往往很不容易彻底克服。这是什么缘故呢?
回答可以很简单,就是因为不虚心。这个回答,应该承认,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复杂情况,对于世界上的一切知识,不可能都懂得,更不可能都懂得那么完全、那么确切。因此,要想对客观的东西认识清楚,就必须虚心。这是对的。
同时又应该指出,虚心却不等于心中无数,没了主张;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离不开主观的作用,只是主观主义才要不得。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对于主观和虚心这两个概念,同样不应该做片面性的解释。
大家都记得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论对待什么问题,我们都应该采取虚心的态度,力求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特别是有许多学术方面的问题,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完全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各抒己见,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过去许多知名的学者,为了追求知识,总是长年累月地向别人虚心学习,虚心问道。这种虚心做学问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取法的。宋代的林逋,在《省心录》中说:“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一为君子,一为小人,自取如何耳。”明代方孝孺的《侯城杂诫》中也写道:“人之不幸莫过于自足。恒苦不足故足,自以为足故不足。”他又说:“虚己者进德之基。”这些都是十分中肯而切要的话。
当然,所谓虚心,既不是心中无数,也不是没有信心。我们对于自己研究的问题,经过反复探讨之后,应该心中有数,做出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