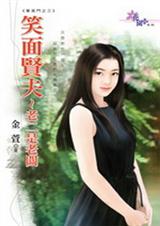这里是老北京-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万点白参差”的描绘。可是后来崇效寺丁香凋零,牡丹葱茂,独以牡丹著称。洪亮吉诗中的旧景,就剩下那句“门前见树尤绝奇”的”故国乔木楸树了”。既多,在北京市是最著名的。解放后建为工厂,将全部牡丹移植中山公园,因为地势关系,移动了两次,合为三迁之荣。不数年死者不计外,勉强活者,寥若晨星矣。可惜佳种一失,即山东菏泽亦难寻觅。可见移植关系,甚宜研求之。请注意最后的五个字“甚宜研求之”,说得何等委婉,其内心早就在流血了。
在我近年研究京城文化之际,这牡丹就越来越给予我一种心象:在中轴线西侧社稷坛“五色土”的四围,同时也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五色旗映照之下,还幸运地环绕着姚黄魏紫一族。它们十分安然又欣欣向荣地生长着,正反映出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的一种延续或凝聚。
说过了中轴线的西边,再去看它的东边。那里是太庙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记:太庙旧时还有一样奇物;就是灰鹤。这是一种在参天柏林中营巢的候鸟,春来秋去,浅灰色,比丹顶鹤小。北京只在太庙中有。《旧都文物略》也记云:“其东林木幽邃,有灰鹤巢其上者千百成群,为它处所罕觏。”太庙进门后东南一大片柏林,旧时四周有栏杆,人不能进去,小立栏杆边,静静地望着林中灰鹤来去,上下飞翔,是充满了寂静的生趣的。我曾多少次和先父来这里,在露椅下静静地坐着,望着那柏树林深处浮动着的阳光、轻雾,从那柏枝密处突然飞起的灰鹤,再过去那高大的红墙外面,就是丁丁当当响着有轨电车的闹市,而这里却那么静,静得似乎那远处灰鹤起飞,拍打翅膀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不禁想起《庄子》上的话,“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息以相吹也。”在这静中,似乎清晰地听着生命的、历史的脚步声……,高大的殿宇前,是有*百年的松柏树林,最古老的柏树要数辽代的了。每年春三月,总会从南边飞来一些灰鹤,它们从江苏北部的湿地起飞,一路左顾右盼,最后飞到华北平原,几经选择,总是在北京太庙上空转几个圈,最后选择松柏树丛降落。它们栖息于此。每天成年仙鹤要飞到中海和南海去“捕”鱼,然后衔回到太庙的树上喂他们的孩子。等感受到秋凉,它们又依照原路飞回苏北……这样的行程不知起于何时,我只知道苏北的那许多湿地是仙鹤家族的祖居之地。有丹顶鹤,有乌羽鹤,也有灰鹤。在北宋的时候,它们是飞向都城汴梁的,宋徽宗画的《瑞鹤图》的下部,是宫殿的屋脊,其檐角高高向天空挑起,虽然国运不济了,但建筑上的气势还在。至于那鹤,似乎不是丹顶鹤,也不是灰鹤。但鹤类喜欢“故国”是有传统的,最近的证据就是《瑞鹤图》。鹤类为什么后来舍弃了汴梁一线,恐怕还是和生态有关。灰鹤选择了北上,同时又一定要栖息太庙,这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但作为一种“天象”或“天意”,就已经让民国时期的北平人士感到满足了。这,似乎是上天的一种赐予,好好善待灰鹤,应该是分内之事。于是,每年在灰鹤降临之后,刚刚变成公园而开放的太庙,工作人员便在灰鹤活动的四围用绳子在松柏树的腰间围绕一圈,游人也自觉不再进入。为了更好地欣赏灰鹤的行止姿态,太庙在绳子外设置了茶座,有雅兴的游人索性坐下来,慢慢地品,悠悠地看。这样,北平便又多了一道新的景观。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梁实秋,其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与他谈恋爱的程季淑,则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梁每次去看女友时,都不能直接进入女子中学,而只能在学校的传达室等待季淑出来。对谈之际,又常因窗外有偷听的女生,他俩觉得尴尬,最后索性“挣扎”出来,一起奔向太庙,因为那是灰鹤到来的季节,季淑又是最爱看灰鹤的。他俩公然在茶座边坐下,这举动在当时是极大胆和极奔放的,引得其他游人频频回望。我猜想,这些人的回望,让梁实秋充满了自豪。我甚至认为,梁实秋后来小品文章之所以写得那么好,跟他这段生活也不无关系。
话锋一转说花鸟(3)
时间忽然来到数年之前,北京某报邀我写一篇介绍台湾饮食文化作家唐鲁孙的稿子。为此我翻阅了他的几本文集。这位老先生实在是位“旗人中的奇人”。他是光绪皇帝珍、瑾二妃娘家的族孙,幼时生活自然是优裕的,成年之后又讨到一份美差,经常可以到各省去吃饭,吃饭是他的副业,而正业是邮政上的视察。他正业一般,而副业极其出色。然而再出色也只是“记在心里”,从没向外边宣扬。这大约也是他旗人的见识,觉得吃饭乃人生的小道,不值得宣扬,自己又不能继续祖先“马上”的功业,甚至因此还有些悲哀。他在1946年到了台湾,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才发觉以撰写文章打发“有涯之生”是个好方法。于是信笔写来,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写了十二本书,在海外华人界内赢得了极大名声。还没等这名声扬至最高点,唐老先生就驾鹤西去。我这次读他的集子,又有了意外的大发现。原来他很早就写过灰鹤,是说它先飞到山东孟子的老家,在其门前的数排高树上住下,每日都从门前河中捉小鱼去喂养幼鹤。有一段话特别生动,因该书不在手边,我只能述其大意:那大的灰鹤把小鱼带回到树上,幼鹤匆忙从窝里出来,扑棱着幼小的翅膀“要吃的”。大灰鹤心说“小东西们呀且别急,你们得等我从胃里边往外‘咳’啊‘咳’”——那些先期吞下胃袋的小鱼,就随着大灰鹤翅膀猛劲地拍打,有些被“咳”出来掉在窝里,小灰鹤扑上前就分而食之,也有些被“咳”出并颠出了窝外,不巧,有些就掉在大树的树杈上了。当地老乡看见,就用竹竿从树干上“梆”这些鱼,等它们掉落于地上,就捡起来煮着吃了。此后,凡是有“噎嗝”毛病而久治不愈的人,只要吃了这样的小鱼,就百分百能够痊愈。我非常看重这段传说,灰鹤不仅是北平城中“能飞的帝王风景”,而且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密切相连,何况它还能帮助孟夫子故乡的人医疗古怪之病呢。有了这几桩优点,灰鹤难道还不值得纪念么?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它们飞临北平就渐渐稀疏了。为什么?多少年连续的兵荒马乱,北平城里城外经常高耸着的枪口,真让它们感到不安全了。但就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们还偶然出没于故宫某些没公开开放的区域的上空。当时朱家溍先生正在故宫供职,他曾多次看到灰鹤在昔日慈禧做寿的翊坤宫翊坤宫在明代时为西宫皇后的住处。清代慈禧住储秀宫时;每逢节日就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据说翊坤宫是故宫最早用电的宫殿,廊子上方的两个铁环据说是婉容皇后拴秋千的地方。想来昔日里阳光明媚的春日,也会有轻衫绿袖少不经事的宫人嬉戏吧。的松柏树枝桠上飞起飞落。再往后,灰鹤似乎就断了踪影。这需要从它的实际遭遇着想:昔日北飞的途程中,湿地越来越少,高楼大厦也冲天而起,它们哪还敢乱飞呢?一些小型飞禽误打误撞飞进北京的公园中,最后被猎枪索命的事,也让这些善良的禽鸟吓破了胆……
这几年,我不断忆念着这些灰鹤,它们与太庙的松树合组成一幅幅的“松鹤延年”图景,属于吉祥的象征。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大量楼盘的开发中,给灰鹤的重新进出北京,“让”出一条安全的通道呢?为什么不能沿途再开出一条湿地的路线,让它们在往返中能够自由栖息呢?
千万别小看这牡丹与灰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上千年的北京的“市魂”。相信今后的外国友人听到这些故事,肯定对牡丹与灰鹤的激情,会超过我们许多倍的。
谈到这里暂告一段。至于如何整治环境,如何使牡丹与灰鹤再生,我将放到后边再讲。真正对北京市有大作用的活动与实践,我将在随后的正文第十章中去谈。第
放眼水系与城垣(1)
说起北京的定都,不能忘记三个人。第一个是元朝的君主忽必烈。早在元朝定都北京前,他带兵从北部南下,来和占据北京的金王朝打仗。金王朝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中都”,中心位置在今天广安门附近。而忽必烈下榻的位置,则在今天北海公园一带,那里有山有水有树还有很好看的石头,忽必烈就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地方。等他后来把金王朝打败了,忽必烈下令定都北京,这就是元王朝的大都了。第二个人就是忽必烈的臣子,是汉人,叫刘秉忠,大概还是个部长级的官员。忽必烈很信任他,把平地建造北京元大都的任务全权交给了他,据说他们君臣之间还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刘秉忠这才全力以赴地干起来。刘在学问上是多面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很懂哲学。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未来的大都勾勒出一个大轮廓:最中心就是言菊朋说的“黄圈圈”——皇帝的宫殿,外边一些则有大一些的皇城“小圈圈”,然后最外边才是那最大的“大圈圈”。大都当时还没有“凸”字形的外城,所以内城城墙就是城墙的全部,也就不分内外了。
以上说的是最简约的北京建城经过。现立于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一侧的滨河绿地上建起的“蓟城纪念柱”,作为代表宣武区的一座城市雕塑,侯仁之教授所撰《北京建城记》一文也镌刻在柱前石碑上。“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其书不晚于唐代,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宫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金元易代之际,于中都东北郊外更建大都。明初缩减大都北部,改称北平,其后展筑南墙,始称北京;及至中叶,加筑外城,乃将古代蓟城之东部纳入城中。历明及清,相沿至今,遂为我人民首都之规划建设奠定基础。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时在纪念北京建城之三千又四十年。”后来,我有一次在侯仁之前辈家中与他闲聊,倒是闲聊中他的一个说法,我以为更实际。他大致是这样说的:“但凡一个城市,总得是位于几条来往大路的交叉点。北京呢,自古就处在三条大路的交叉点上,一条是东北来的,一条是西北来的,再一条呢,就是从北京向西南延伸,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