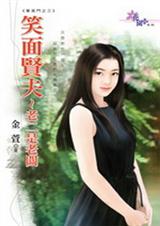这里是老北京-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北京的形象(1)
京剧《梅龙镇》中,李凤姐用京白探问微服私访的正德皇帝:“您——您,可住在哪儿啊?”正德则用韵白回答说:“我么?就住在北京的大圈圈中,大圈圈中有个小圈圈,小圈圈中又有个黄圈圈……”
这三个圈圈相互套着的城市,就是咱们的北京。这样的表述,应该承认它形象生动,比地图也差不了许多。再往深处与好玩处说,并不是所有的京剧老生都这样念,据马(连良)派弟子张学津讲,他1976年奉命排演此剧,是上边要他按照言(菊朋)派的路子这样念,上边同时还宣布,李凤姐需要用程砚秋的声腔。可一查,程砚秋生前根本不唱这一出。于是没办法了,就只能委派程派传人李世济为李凤姐配声,再由荀派弟子刘长瑜为之配像。诸位看官注意,我可不是跟您在谈京剧轶闻,只不过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生活在这三个圈圈当中的梨园人物,对于京城大圈圈的态度与无奈。
言菊朋(1890~1942)是京剧言派声腔的缔造者,也是梨园圈中一位比较有文化的演员。至少可以说,他创造的这个流派比较有文化,虽然欣赏者的圈子不够大,但层次却非常高。二十年前,李世济正在排演我为她写的京剧《武则天》时,她主张同团的老生张学海(学津的同胞兄弟,麒派传人)演唱中要多向言派靠拢。我记得有一次在世济家中,突然小平夫人派通讯员送来言派三代人(言菊朋、言小朋、言兴朋)的声腔录音,请其转给张学海创造人物时作参考。我当时看在眼里,却什么也没说。梨园人都知道,*是最喜欢听言派的。
又说多了。容许我笔锋一转,转到五四之后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是怎么看待与怀念北京的。
李大钊:《黄昏时候的哭声》《黄昏时候的哭声》写作于1921年3月5日,刊载在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编辑创刊的《新生活》周刊第46期上。彼时的北京正在奉系军阀的控制之下,南北尚未真正的统一。同日,正在浙江奉化韬光养晦的蒋介石,奉书孙中山,建议缓选总统,以免“难以俯顺各方”势力,“仍蹈民国七年之覆辙”。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青年才俊时的蒋中正,在国家危乱时期,那种“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忍下咽”的报国情怀。
北京市内,每到吃晚饭的时候,有一种极悲惨的声音送入市民的耳鼓,这就是沿街叫苦乞怜于阔人家残羹剩饭的呼号。这种声浪,直喊到更深,直喊到断断续续的不绝。一家饱暖千家哭,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忍下咽吧!
陈独秀:《北京十大特色》《北京十大特色》写作于1919年6月1日,收录在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卷二中。文中描写的京城十大特色,虽说是出于洋风熏染后的“国人”视角,却多少反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后的不久,北京街头上特有的世相。陈独秀在此文后的两日,又有题为《六月三日的北京》的文章。“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此种心情下,来看“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的议论,可知所谓“特色”之后的隐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京的形象(2)
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他说在北京见到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色:一、不是*时代,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二、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三、汽车在很窄的街上人丛中横冲直撞,巡警不加拦阻。四、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线。五、十二三岁小孩子,六十几岁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加干涉。六、刮起风来灰沙满天,却只用人力洒水,不用水车。七、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八、分明说是公园,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九、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十、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
周作人:《前门遇马队记》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一位读书人出北池子向南行走,遭遇了军警马队的呵斥驱逐。他惊恐万状地从天安门往南,沿千步廊,穿中华门,到达前门,才长吁一口气。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前门遇马队记》,讥讽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谈虎集》)而今天的读者却从中不经意地感知到中华门的存在。这个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名叫周作人,他走在已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广场上。这一天,距离五四运动刚好两个月。(来源:《北京晚报》)
*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去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到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些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站立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的。但我想兵和我一样是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向前去。我对他们说,“那班人都是我们的中国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们则说,“你不要见怪,我们也是没办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地站着,却不料忽然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边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往北直奔,后边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这“履中”两个字的牌坊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地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对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马上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于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去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中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想到这里,不觉已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再要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从不曾受过兵警的呵斥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绝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起所受的侮辱更大。
北京的形象(3)
冰心:《默庐试笔》《默庐试笔》是1940年冰心在云南呈贡时,应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之约而作。“默庐”是冰心给自己当时的那座祠堂式住所起的斋号。杨刚与浦熙修、子冈、戈扬齐名,是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女记者之一。1937年7月28日,冰心笔下“不挣扎不抵抗之后”“便恹然死去”的北平,事实上,在日军向北平郊区发动进攻时,当时的中国守军与之展开了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当日阵亡,成为中日大战最初为国牺牲的高级将领。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死去了。
二十六年(1937)七月二十八早晨,十六架日机,在拂晓的晨光中悠悠地低飞而来,投了三十二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但这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色!海甸被砍死了十九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当作了散兵、游击队,有被砍死刺死的危险!
鲁迅:《长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并分析说,“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北之种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中山此论,与贾谊《过秦论》、陆参《长城赋》中“筑城祸国殃民”的论点大相径庭,亦与鲁迅《长城》中“伟大而可诅咒的”的观点差强甚远。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吧。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如何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俞平伯:《进城》《进城》写作于1933年11月2日,收录在《人生不过如此》集中。文中所提到的海甸镇,位于北京西北。在近人许觉民笔下的1957年时的海甸镇,依然“很小,走出书店,穿过一条小巷,就是田野,我们在田野里边走边聊,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黄昏。自此,我们相约,每日黄昏在校外相见”。当时政治生活诡谲,和他聊天漫步的那个人,就是后来“*”中轰动一时的抗暴英雄——林昭。
公共汽车于下午五点半进城去。
圆明园是些土堆。以外,西山黯然而紫。上边有淡薄橙色的晕,含着一轮寒日。初冬,北地天短,夕阳如箭,可是车儿一拐,才背转它,眼前就是黄昏了。
海甸镇这样的冷落,又这样的小,归齐只有两条街似的,一走就要完。过了黄庄,汽车开到三十里上下,原野闪旋,列树退却,村舍出没……谁理会呢,不跑得够了,瞅得腻了么?谁特意向车窗伸眼呢。这些零星的干黄惨绿也逐渐混融在不分片段、灰色的薄霭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的形象(4)
“分明一路无话,也是文章吗?冤人。”原不知是不是。万一而“有话”,那决不外轮胎爆裂,马路抛锚,甚至于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车仰人翻,再甚至于《水浒传》式的一声大喊,连黄棉袄也会摇摇的,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