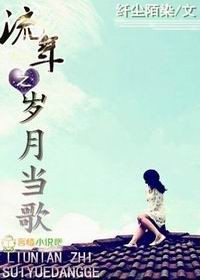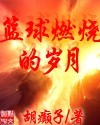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
苏联高校的学术风气是开放的。
在苏联的大学里,至今保留着一种叫做“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中文译称讨论课)。课前,老师就某一讨论课题布置作业。课堂上,通常以一个学生的主题发言为开端,大家展开讨论。学生们争先恐后、畅所欲言,经常会就某个问题争执起来,火爆的场面层出不穷。
记得我刚进入苏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习明纳尔”的课堂上还不好意思开口,怕说得不好“丢面子”。后来我才体会到,在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鼓励学生勇于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有条理、有依据地表达出来,在激烈的意见交锋中阐释、完善、捍卫自己的观点。这种日复一日的锻炼,对于学生们培养开放交流的心态和坚持己见的勇气是大有裨益的。
有赖于开放的学术氛围,苏联的大学成为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共存与竞争的舞台。而苏联人直率的性格,又使得不同观点的交锋显得格外尖锐。
第八章 润物无声(2)
许宝文对此深有感触:
“在学校里,经常会有某个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会。会场上,同行,甚至同事间会为某个学术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争得面红耳赤,丝毫不留情面。这令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庸哲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开始感到不太适应。
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做了成果介绍之后,系里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权威马上站起来说,‘你讲的东西,在理论上和证明上根本站不住脚。……’不料那位年轻人毫不让步:‘你提的问题实在没有水平。你要我证明的东西,就像要我证明我自己不是一头骆驼一样毫无意义!’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对话,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再次见到他们,两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苏联,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展开正面交锋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会牵扯到学术以外的其他乌七八糟的事情。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论是真知,还是谬误,都在面对面的褒扬针砭中浮出水面。对科学真理的认知,就是在不断的争论和证明中向前推进的。相反,那种‘和事佬’的作风,才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之高,学术精英群体之雄厚,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学术泰斗并没有深居象牙之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完成自身科研任务之外,还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
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全苏科学院院士的身影。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U27'教授向我回忆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
“我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他指导的研究小组,根据概率论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数法则,进行了不间断地统计学分析,饶有趣味地发现了许多“相关”,证明在某种人群中相关的概率。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得到了公安机关的重视。据说只要知道了某一根手指的某一骨节的长度,就可能根据统计概率推断得出身体另外部分的值,从而对破案有所帮助。在与他并肩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会了如何发掘数据、如何认识事物、如何持之以恒、如何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和他一起完成这项工作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好几位大科学家。”
苏联教授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钱凌白深有感触:
“在我所就读的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有很多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设计专家。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同时还在国家的设计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因此,他们讲课时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马春途对他的几位苏联老师至今津津乐道:
“克雷洛夫少将是教我们概率论的教授。他结合莫斯科防空作战的实例,讲述概率论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莫斯科防空战是二战中城市防空作战最成功的战例。而克雷洛夫本人作为苏联概率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当时正是受命参与城市布防的设计。他运用概率论的知识,计算出敌人为了实现理想的轰炸效果,会调用多少架飞机,而我方应当如何布防地面防空炮火,以实现最好的打击效果。实际作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一门看似枯燥的概率论,由于有了实际、精彩的案例,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第八章 润物无声(3)
还有一位老师,曾是苏联空军战斗英雄,退役后进入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并任教。他开了一门课,叫做‘飞机机动学’。这门课讲的是在敌我双方战斗机高速相对运动过程中,如何通过速度、高度的变换,占据最有利的战术位置。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数学、力学的运算。这是很独特的学科,完全建立在教授本人的实战经验和理论升华的基础上。直到现在,我在国内外的各种空军教材中,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内容。”
苏联老师不仅自身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也极力要求学生们重视实践,关注细节。对于苏联老师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学习应用科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王邻孟'U28'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有一位教我们农业机械化的老师,他的实践能力很强。到新开发的生荒地支援夏收时,生产队的机械坏了,他自己都能够动手修理。考试时,他会经常跳出书本,问一些需要在实习的过程中用心观察才能发现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问一名学生,联合收割机割下的草从上面走还是从下面走,那个同学答不上来。他就要求那个学生马上出去找一台机器观察。”
研究生专业最低考试的过程令陈国藩终身难忘。
在流利地回答了若干问题后,导师突然问道:“请你告诉我,各种吊机的司机室位置都在哪儿?”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陈国藩一下子懵了。
在国内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自己一直是与书本打交道,几乎没有去过施工现场。导师只是通过一个问题,便发现了他缺乏实践经验的缺陷。
针对这一情况,导师特地为陈国藩安排了大量的实习。在喀山桥梁施工现场的漫天大雪中,陈国藩穿着欤B鞋,滑着雪橇穿行于住所和工地之间,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陈国藩感叹道:
“师从于这样的导师,心中怎么可能容得下半点浮躁和虚伪呢?苏联很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也正是我国教育的薄弱之处。”
张开华则是通过“大跃进”时的一件小事,领教了苏联学者的“较真”:
“大跃进期间,国内有的地方放出了亩产万斤小麦的 ‘卫星’,报纸上还出现了小孩子端坐在密密匝匝的谷穗上的照片。我们留学生们欢欣鼓舞,拿着照片向老师炫耀。
一位乌克兰农学院的老师认为不可思议,他来到基辅工学院找我们了解一亩地相当于多少公顷。在详细了解了一些细节后,他摇摇头说:‘这不可能吧?这种密植的结果是完全不透风啊?’我们也不太懂农业知识,无法说服他。没想到,他真的到自己家的田里,按照我们报纸上公布的耕作方法,搞了一小块试验田。不久,他又找到我们,生气地说道:‘你们的数据严重失实。中国人不诚实,这样下去对你们是不好的。’”
在苏联教师所具有的诸多优良品质中,“敬业”也成为中国留学生屡屡称道的一点。
一位学长回忆道:
“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看到窗外下着大雪,树枝都被压断了。同室的苏联同学说不会有人去上课了。作为一个中国学生,我是不会因为天气而缺课的。我和另一个中国同学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齐膝深的积雪赶到教室。铃声响过,教室里只有我们###学生,和一位苏联学生。正当我们议论老师是否会来的时候,教授带着一身的雪花和寒气闯了进来。他一边抖落身上的积雪,一边为因交通受阻而道歉。他显然没有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学生而失望。他为我们三个人讲了一节课,一如往常的生动和深刻。这无疑是我留学期间听得最入神、印象最深刻的一节课。”48
对此,我深有同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苏联高校教师的待遇颇高,住房条件优越,很多人还买了小汽车。九十年代初,社会变革到了最痛苦的阶段。大学教师们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以至于要在郊外种些土豆、蔬菜养家糊口。
第八章 润物无声(4)
尽管如此,学院里课程仍然正常进行,教学质量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在课堂上,老师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引发对时局的感慨。可是三两句抱怨之后,他们总会挥挥手说道:“算了,不说了,我们继续。”
或许,就在上课之前,他还在为生计忧虑;或许,就在下课之后,他又要奔向兼职的岗位,为第二天的面包奔波。可是就在这里,在课堂上,他就是知识王国里至尊的国王。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压力,全身心投入于科学研究的乐趣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然物我的乐观主义的存在,前苏联的科学巨树才得以保留下高贵的血脉,并且在经历了最严酷的季节后,重新萌发出新的枝干。
然而,最令中国留学生们景仰的,是苏联知识分子捍卫科学真理、不迎合世俗与政治淫威的高贵品格。
马春途回忆道:
“我对一位讲授苏联军事历史的叫做季莫霍维奇的教授怀有很高的敬意。
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时候,他还是客观评价斯大林在指挥战争中的功绩。有些东欧国家的学生在课堂上提出:‘斯大林已经被打倒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现在还适宜再提吗?’季莫霍维奇教授当场正色道:‘我讲的是历史,历史是不能随意篡改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一直牢记到现在。”
曾在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学习的刘恕向我讲述了一位名叫达尔曼的老师的故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在生物遗传学领域存在着两大学派。一派以米丘林为代表,认为动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