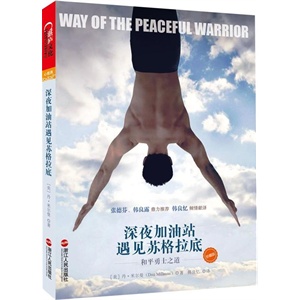如若不曾遇见你-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未待聂霜开言,冥翳便截口含笑:“既知晚,便该甘心受罚。”
“王爷准备如何罚呢?”我唇角微翘,眼波流转问道。
冥翳笑不多言,狡黠着执起桌案上白玉羊脂酒壶,微倾壶身便有一小股琼浆玉露滑进他手中薄杯,酒香如蜜,色泽雪白,似是皎皎月白银华。
他轻抿一口,脸上犹自意犹未尽,末了,他将剩下的半杯递与我。我略略迟疑,但还是含笑着接了,环视在座其他人,钟离荷娇怜盈盈,凝笑于眉间,柔柔地瞧着我;梅归则埋首低头,轻饮浅啜,似周遭热闹独独不属于她一般;最令人捧腹的大抵是聂霜此刻的表情了,那绯色脸庞因着过度的激动与愤恨,愈加像开败的残花,红艳依旧花形无存。
我敛眉低目,掩袖举杯一饮而尽,生怕聂霜眼中喷射向我手中酒杯的万丈火焰,将我杯中酒瞬息蒸腾。不过是别人喝剩的残汁,巴巴地有人将之当成瑶池甘露!
“如何?”冥翳柔声低问。
我浅浅一笑,还递酒杯于他掌中,“不羡凉州琥珀光,不须少妇郁金香,侬家新酿梨花白,相约临翁共举觞。”
冥翳唇角的笑意更深:“你懂得倒颇多!这洛阳梨花洗妆,甘醇清冽,饮之如蜜,本是酒中翘楚。”
“要不怎的古人有诗曰:青帘沽酒趁梨花。”
彼时此间仿若就只剩我与冥翳二人,绕酒畅谈,偶有盈袖暗香浮动,销魂无数。他毫不掩饰对我的直白深情,点漆黑眸中,那情愈深,我的心愈不安,而聂霜脸上的神色亦愈难看。
喧宾夺主并非我本意,冥翳旁若无人的专宠无疑是一种罪过,这罪孽势必会报应在我身上,造成严重的后果。他是不杀伯仁,而我这伯仁却因他而死。
我侧身吩咐阿珊娜,将我从欢颜斋所得之香赠与聂霜。那香瓶用的是大食国上等琉璃制成,瓶口、底座、瓶颈以及瓶腰皆用金粉细细勾勒,宛若一位美丽的舞娘特地以珠宝装点她身上最美丽的部位。
我点水无痕般扫了一眼聂霜的神情,有雨过天晴的征兆。她果真是嗜香如命,我暗自思忖。
“妹妹生辰,做姐姐的愚钝,原是想不出什么好花样搏得妹妹欢心,念及妹妹素喜香,遂浅备薄礼,还请妹妹笑纳!”我嫣然笑着婉转道。
聂霜颇为欢喜地接过香瓶,媚声道:“那我就多谢姐姐了。”
她忙不迭的掀开瓶盖,室中顿时弥散着一种奇异的香味,闻之令人感觉有种神秘的惘然,但又使人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可就是在众人恍然之际,我注意着冥翳骤然猛喝尽杯中酒,淡淡对聂霜道:“霜儿,今日本是你唱主角,不妨便为我们舞上一曲可好?”
聂霜笑靥如花,灿然道:“能为王爷与在座诸位姐妹舞上一曲,聂霜求之不得。不过,聂霜有一个不请之情——”
冥翳淡定道:“你说。”
聂霜微微一笑,便转向我:“妾身早闻姐姐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皆精,今日,妾身斗胆,烦请姐姐抚琴一曲,妾身和曲起舞,不知姐姐意下如何?”
当下,室中所有人目光皆凝聚于我身。我还来不及细想推脱之辞,聂霜便又笑对冥翳:“王爷,想是妾身身份卑微,这样无理的请求,倒教姐姐难为了。”
冥翳旋即含笑对我道:“君善抚琴依善舞,琴舞双绝两相宜。梦蝶,勉为其难吧!”
我暗地里咬碎了满口银牙,却只能和着不满往喉咙里咽。聂霜这招釜底抽薪,够狠!使我骑虎难下,她够聪明!只是,她算准了我不会弹琴么?
第二十六章 阁中帝子今何在(二)
“王爷,前日里偶遇王妃娘娘,得知娘娘这几日身体微恙。要知弹琴者最是耗费心神,不如今日就让奴婢替王妃娘娘弹奏一曲,虽感班门弄斧,不自量力,却也是奴婢对娘娘、对夫人的一番挚诚心意。”
我循声而视,钟离荷盈盈起身,离开自己座位,莲步移自厅中,俯首柔柔说与冥翳。
“梦蝶,你身子不好么?”冥翳关切问,眼中却是亮如晨星。
他一日里倒有半日时光与我待在一起,我身子好坏他自是比谁人都清楚。
我微欠身,无谓道:“天气变化无常,想是有些着凉。”
冥翳微点头,嘱咐我在左首席入座,然后笑对聂霜:“霜儿,钟离琴艺高绝,定也不会辱没你惊鸿一舞。”
他话甫一出口,我暗自松下一口气。弹琴?天知道我只要对着那琴弦,便似飞娥缀了蛛网,只怕是灰飞烟灭、粉身碎骨也再难拂去我心头的伤痕。那是我的死结,也是我致命的弱点。可是今夜,我居然轻易让别人抓住了这个弱点。
聂霜对着我娇笑连连,语声亲切绵软:“虽然不能聆听姐姐天籁之音,实在遗憾,可姐姐保重身体当属要紧。”
她一面说着,一面吩咐下人抱琴而至。
相如绿绮琴,佳人端坐,右手拨弹琴弦,左手按弦取音,不过是脉脉拨弦三两声,便如流水洗客心。
我心不禁一颤,那一曲琴声幽幽,销尽红尘万古悲愁,清音袅袅,悠扬婉转。聂霜随曲而动,风姿洒落,衣袂翩然,弄影厅堂,舞着满室流光溢彩,舞尽瑶台半生倾欢。
冥翳脉脉含笑,眼神随聂霜一同飞舞旋转,眉宇荧荧,百感魂翩。
绿绮为谁弹?琼花为谁舞?刹那间不就通透明澈么。
曲尽舞散,厅堂中余音袅袅,香雾遍染。我执杯饮酒,酒入喉咙,原来梨花白也能让人产生辣辣的生疼。
撤琴而去,钟离荷入座之时,七分了然地对着我微颔首浅浅一笑。裹起心绪不宁,我对她回应一笑,今夜,我始终是要感激她的。
接下来的席间,梅归让玄圭捧出一约三尺长的雪白画卷,叫了另外两个下人,分执画卷两端。梅归双手执笔,翩然起舞于雪白画卷之前,边舞边画。霎时,墨香迎风飘飞,长袖当空吹散,花怒放,影徘徊。一舞尽,画已成,那原先雪白的画卷上赫然多了一丛栩栩如生的芍药,叶绿花红,艳丽绰约,花旁更有两行小篆:万花竞纷华,无双独此花。
梅归将此画赠予聂霜,复又向众人敬了几杯酒,薄醺微醉,便向冥翳告了辞,在玄圭的搀扶下离了水月阁。
聂霜一舞动地,兴致越来越高,加之她是今日宴席中的主角,冥翳对其十分地纵容,在整个夜宴中她算是风头出尽。相较之下,我既未展现才艺,也未欢声笑语,越发衬得自己落落清影。
曲终人散,已是夜半时分,聂霜借着酒劲儿紧紧抓住冥翳不放手。我扫了一眼那情景,漠然一笑,缓缓离去。冥翳一边扶住摇摇欲坠的聂霜,一边急切地在身后唤住我:“梦蝶——”
我悠然转身,便又是一腔平和:“午夜流风,王爷切莫让聂霜妹妹受了凉,有什么事待明日再说。”
我自不待他开口,便尾随钟离荷离开。外间寂寞夜空,如墨泼洒的漆黑,凉凉夜风,居然引得身上战战生寒。
第二十六章 阁中帝子今何在(三)
在我的记忆中,爨族的气候向来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终年苍翠满城,花枝不断,四时如春。襁褓之中,估摸着睁开眼看到的,第一是母亲的笑靥,第二便是碧蓝的天空。
很多年前的有一日,天居然出奇的暗黑,仿若遮着厚厚的漆黑帷幕,空气潮湿而闷热。午后,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一注一注,惊心动魄,疯狂肆虐。我害怕着躲在窗后,不知为何,手心原本的温度就随着眼前的激烈渐失,心中莫名升腾起酷寒的森意。
我转身便往外冲,却被阿珊娜一把从背后抓住了我的手。
“公主,你这是去哪里?”
“我去看看母亲。”
“待雨停了再去也不迟。”她并没有放开我的手,反而抓得更紧更牢。
我心下烦躁,像有一颗不安的种子在心底即将破土而出。想也没想,空闲的那只手出奇不意狠劲地抓过阿珊娜的手背,顿时,阿珊娜雪白的手背上赫然多了几道鲜艳的血痕。
“你放不放手?”我顾不得她的伤痕,只是固执而又恶狠地吼着她。
阿珊娜愣愣地望着我,也许她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对待她。她的眼眶有些微红,表情也有些僵硬,但是很快,她依言默默地放开了抓紧我的手。
这世上,她比谁都了解我的坚定。
“奴婢为公主取伞。”
我默然点头。
母亲的寝宫很安静,安静到死寂,死寂到令人恐惧,仿若外间哗哗的雨声并不是真实。什么时候,这里居然没有一个宫人,我的心飞速地跳动着。
帷幔一层层密不透风,穿堂风吹过,帷幔寂寞地晃动着。光线很暗,看不清宫中的陈设,隐约觉得空气中还浮动着瑞龙脑散发出的暗香。我母亲最是喜欢明媚灿烂的阳光,即便是在墨黑的夜里,长信宫灯也必是燃得四壁生辉。
“母亲!”我忐忑不安地低唤着,却没有人回应我。
举手撩开华丽的重重帷幔,几个穿梭,来到母亲的卧室外,门开着,里面除了灯火,还有人说话的声音。
“王后,都到这份上了,这琴弹与不弹又有什么关系。”
我一惊,这男人的声音,很熟悉,可却一时想不起是何人。
母亲似乎没有理会他,很快,一曲琴音回荡在孤寂的寝宫,缠绵幽怨,如残花的凄迷与落寞,断人心肠,欲咽还噎。平日里,但凡母亲弹琴,我总是静静聆听。母亲为我弹奏的曲子一向婉转动听,欢快明朗,悄悄拨动我心弦的时候,似在眼前展现出一幅幅清新的山水画。可是现在,母亲正弹着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悲凉曲调,酸酸痛痛地折磨着我的心。
卧室的菱花铜镜正对着门,镜里是母亲消瘦憔悴的容颜,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眼神是无边的绝望与悲怨,卸了凤冠璎珞,一头乌黑的长发直落身后。
琴声越来越急,尖锐刺耳,竟让人觉得如半夜恶鬼凄凉嚎叫,令人毛骨悚然。母亲低头专注于琴弦,两颊的长发遮住了半张脸。突然,“嗒”的一声,琴弦因无法承受剧烈的张力猝然绷断。
“琴断人完,呵呵。。。。。。”母亲骤然抬头,凄厉的笑,脸上纠结的青丝,情丝却是随弦而亡。
那个男人略微叹息了一声,“曲终人散,娘娘便喝了这酒,奴才也好回去向王交待。”
奴才二字,让我突然想起这个男人原是父亲身边最信赖的宦官乜(mie)达。他在劝母亲饮酒,此时此景,我母亲能喝下什么酒呢?
母亲缓缓地起身,面无表情从乜达身后的一侍从盘中接过那杯酒,“这酒颜色真好,真像鸩鸟眼睛里的血红。”
“这酒的味道也很好,而且它不会让娘娘有任何的痛苦。”
“是么?”母亲冷笑,一倾杯,那酒便全数倒在了地上。
“娘娘何必为难奴才!”乜达也是冷笑着。
“他不过就是要我死,难道只有鸩酒才能要了我的命?”母亲忽然淡淡地开口,话语里是掩不住的嘲讽。
死?鸩酒?我隐在门外阴暗处,撕心裂肺的痛在胸口一阵一阵的荡漾。
“那奴才无礼了。”
我忽然听得里间有挣扎的声音,还有触碰琴弦嗡嗡的声音。无边的寒意袭上我的背脊,痛苦、恐惧像铁钉一样将我钉在了冰冷的大理石地面。突然从耳际传过母亲喉咙发出的沙哑沉闷的咕咕声,我再也忍不住地挪足走向门口。
“娘——”我竭尽全力地呼喊,却只是嘴里做出了喊叫的口形,无声而绝望。那一刻,比痛苦更甚的是驱散不走的恐惧。
母亲的脖子上,是一根细细的琴弦,像毒蛇一样凶狠的绞紧,鲜血不断地从勒处漫溢,惨白着脸,嘴角流淌着刺目的血红。那弦的两端执在两个侍从手上,那两双手背上的青筋暴露纠结。
母亲最后望向我的那一刻,是诡异的淡笑,不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