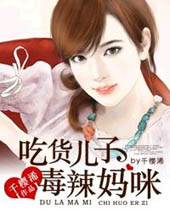山人孟夫子-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发的前一天,蕙玉默默地为丈夫准备着行装。她知道,丈夫这一去至少得一年。四季的衣物靴帽都得带齐。
甫儿已经满十六岁,颀长而瘦峭的个子,极象他的父亲。他不停地帮着父亲整理笔墨纸砚和一些书籍,已经装了满满的一大箱。
孟浩然正在精心地擦拭那把弹了多年的古琴。
“爸,路途这么遥远,还带那玩艺干啥?”甫儿不解地问。
“等我想你和你母亲的时候,就弹上一曲解解闷儿。”浩然笑道。
“您现在就给我们弹一曲吧!”甫儿恳求着。
“好吧,父亲今日高兴,就给你弹一曲《示孟郊》吧!”
琴声悠悠地响起,甫儿也跟着音律轻轻地哼着:
蔓草蔽极野,兰芝结孤根。
众音何其繁,伯牙独不喧。
当时高深意,举世无能分。
钟期一见知,山水千秋闻。
尔其保静节,薄俗徒云云
母子俩默默无语,静静地听着。一家三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孟浩然意犹未尽,又自弹自唱了一曲《寒夜》:
闺夕绮窗闭,佳人罢缝衣。
理琴开宝匣,就枕卧重帏。
夜久灯花落,熏笼香气微。
锦衾重自暖,遮莫晓霜飞……
听着听着,蕙玉的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也轻声唱道:
一别隔炎凉,君衣忘短长。
裁缝无处等,以意忖情量。
畏瘦疑伤窄,防寒更厚装。
半啼封裹了,知欲寄谁将。
“母亲,别哭。父亲这次一定高中的。”甫儿懂事地安慰着。
夜深了,大家都还没有睡意。厮守在一起聊这聊那,好象有说不完的话。
第二天,南儿起得很早。他把两匹马刷得干干净净,鞍辔鲜明,连马蹬子都擦得雪亮。然后,又用上好的草料把它们喂得饱饱的。
离开涧南园的时候,蕙玉和甫儿,孟老爷和老太太,哥哥馨然和谔然,从弟邕儿,姐姐适莫氏;还有王迥都来送行。
“浩儿,咱老孟家能否出人头地,就寄希望于你了!”孟老爷今日特别高兴,眼神里充
满着无限的期望。
“祝你好运!”王迥握住孟浩然的手。
“父亲大人,白云弟,你们都保重!”孟浩然拜别家人好友,扭头翻身上马,携孟南向北急驰而去。
第一天上路,人和马都精神抖擞。除了晌午在一个偏僻的小饭铺胡乱填了一下肚子,给马儿喂了一些草料外,一直在路上飞奔。马蹄得得,快疾如风。黄昏时分,便抵达了蔡阳。
天气昏沉沉的。孟浩然和孟南便下了马,寻了间僻静的客栈投宿。
客栈虽小,倒还清净。透过窗户,可以隐隐约约看见远处模糊的山丘,树林和庄稼地。这些在孟浩然看来并不觉得荒凉。因为这儿跟涧南园太相似了,反倒有点归家的感觉。
屋外,老北风嗖嗖地刮着。疲倦的南儿早已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孟浩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咋也睡不着。也许是对明春的进士考试有一种充满信心的期待吧,他的心情有些激动。不禁轻声地哼道:
日暮马行疾,城荒人住稀。
听歌知近楚,投馆忽如归。
鲁堰田畴广,章陵气色微。
明朝拜嘉庆,须着老莱衣。
“公子……一定高中……”
这声音突然把孟浩然吓了一跳。原来是孟南在梦中呓语。他笑了笑,连忙披衣起身,帮南儿掖好蹬开的被褥,然后吹灭了蜡烛,打了个呵欠,又钻进了自个儿的被窝。
天刚拂晓,孟浩然主仆二人起了个大早,继续前行。
空中布满阴霾,天气依然昏沉沉。通往长安的大道上,行人稀疏。车辆缓行。唯有孟浩然主仆二人的白马在昂首飞奔。
行至途中,忽然北风呼啸,下起了大雪。刹时间,大朵的鹅毛团飘飘洒洒,给远处荒凉的山川丘陵,田野林木披上了茫茫的素装。
雪越下越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漫长辽远的古道两旁,荒无人烟。孟浩然和南儿别无他法,只得顶风冒雪,继续提笈负琴,策马前行。
这雪一下就是好几天,整日不见阳光的阴霾天气,大雪连阴的寂廖山野,使形单影只,远离家乡,孤独客行的他平添了几分无助的乡愁。
漫天皆白,疲倦消瘦的马儿喘着气嘶鸣着,低首慢行。风雪弥漫中,一群迷路找不到沙洲栖宿的大雁扑腾乱飞,几只饥饿的野鹰凄然地哀鸣着着,给孟浩然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阴影。尽管此次进京赴举,他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但也难免有几分前程莫测的茫然。他忽然觉得,那无处可归的大雁,和凄惶的饥鹰就好象是瓢泊在大雪中的自己。
孟浩然拍去衣袍上的积雪,伥然叹息:
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
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
落雁迷沙渚,饥乌集野田。
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
孟南对主人道:“公子,天色已晚,路途难行。前面有几间茅舍,我们暂且住下,明日再行吧!”
17盛唐诗杰京城相会 王孟双双相见恨晚
天气终于渐渐地晴了。
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虽然风刮在脸上还有点冷,孟浩然的心情却好了许多。他和孟南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往京城赶去。
进入渭南平原,路好走多了。离京师越来越近。当望见长安那雄伟的古城墙时,孟南竟高兴得象个孩子,“啪啪地”甩着马鞭,欢呼起来。
进了城,那都市森严的三内九衙,繁华的两市百坊,富丽的玉楼琼阁,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令孟南感到既新鲜又好奇。他左顾右盼,只觉得眼花缭乱。
孟浩然笑着催促道:“傻小子,日子还长着哩!先找个地方住下。以后会让你看个够的!”
很快,他们在皇城大街的最南端附近找到了住的地方。这里叫布政坊,在皇城的西南端,出门就是东通春明门,西通金光门的皇城大街,方便得很。特别是每一坊都有围墙,四面各开两个大门,朝开夕闭,有雄壮威武的执金吾,彻夜巡逻守卫。
坊内有一位刘姓官宦之家的院落。因为升迁的缘故,主人带家眷到南方赴任去了,因此,这房子就空闲了下来。
一位负责守房子的老翁带着孟浩然把刘家大院里外都看了一遍。除了正屋之外,东西各有一排厢房。那东厢房稍大,有三间,已经租了出去,就剩这两间小一点的西厢房了。这厢房倒清洁、僻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孟南向来干活麻利,三下五去二,行李、床铺、书案都收拾好了。
“公子,一切收拾停当,带我出去逛逛吧!”
“我说你这会儿干事咋象一阵风似的,原来,你的心已经野了。”孟浩然笑道。
主仆二人刚准备出门,忽然传来一阵乐呵呵的叫嚷声:“刘师伯,添新房客了?这下可热闹了。”
“王公子,您回来了?这新来的孟公子也是位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哩。”刘师伯欣然答道。
听说东厢房的房客回来了,孟浩然正思忖着是不是去去拜访一下,那房客已经先过来施礼了:“孟公子,您好!”
孟浩然抬头一看,此人不过三十岁左右,皮肤白皙,风姿俊美,文质彬彬,风流倜傥,心中顿生敬意,慌忙还礼:“在下襄阳孟浩然,拜见公子。”
房客惊讶道:“您就是那‘春眠不觉晓’的孟浩然?”
“正是鄙人。”
“久仰、久仰。在下姓王名维,字摩诘,太原祁县人氏,还望日后多多指教。”
那房客又要施礼,被孟浩然一把拦住:“太原王氏,乃五姓望族。怪不得王公子气度不凡。原来是名族之后。听说公子自幼聪颖,九岁时便能作诗写文章,而且工于草书隶书,娴于丝竹音律,擅长绘画,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如此客气,羞煞吾也?”
“彼此,彼此。浩然兄过奖了!”
两人一见如故,便坐下叙话。
“孟兄此次来京,所为何事?”
“鄙人年届不惑,却来京城应试,说来可笑矣。摩诘兄,你才华名扬天下。开元九年二十一岁时就中了状元,即解褐为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为何今日又闲居此处?”
“唉,一言难尽。那不久以后,因为署中伶人为岐王舞黄狮子犯禁,我被牵连而谪为济州司法参军。”
“犯了什么禁,如此严重?”
“那黄狮子只能舞给皇帝看,是不能舞为其它王公贵族舞的呀!”
“那是岐王的事,与你何干?”
“浩然兄有所不知,那歧王在吾应举时,请公主帮过忙。待吾恩重如山。还有宁王、薛王待吾就象师友一样。故而被牵连矣。”
“后来呢?”
“其实,我心里明白。皇上与诸王向来不和,矛盾颇深。京城不可久留。当年秋天吾便离开京城,赴济州任。好在当时同乡诗友裴耀卿任济州刺史,与吾情同手足,使吾稍得安慰,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但裴刺史很快又赴宣州任职,使吾失去依靠,甚感惋惜。开元十四年春天,吾也辞去司法参军之职。离开济州后,又在淇上住了二年。刚来长安闲居,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习顿教,”
“唉,真是官场险恶呀!”
“不谈这些了。天色已晚,浩然兄初来乍到,多有不便。今晚到寒舍小酌如何?”
浩然欣然从命。来到东厢房,他看到王维的住所十分简朴,甚为惊讶,丝毫也看不出曾是一位中了状元做过太乐丞的人。
王维向夫人介绍道:“这位是我们的新邻居,来自襄阳的孟浩然孟先生。”言毕,又扭头告诉孟浩然:“这是拙荆。”
王维夫人递上一杯香茶:“昔日我曾听官人说起过孟先生。没想到今日竟做了邻居,真是有缘。”
孟浩然听王夫人说话言词得体,语调柔和,再仔细一瞧,她眉清目秀,端庄大方,一看就是位温柔贤惠的妻子。孟浩然觉得,在她身上依稀有蕙玉的影子。
不一会儿,王维夫人已将一桌酒菜备好,孟浩然就与王维各自落座,对酌起来。
“凭浩然兄的才华,此次应试,定当一战而霸。”
“那里那里。当年你高中时,有歧王引荐,公主帮忙。而我朝中无人,恐难及第。”
“丞相张说不是很赞赏你吗?浩然兄何不拜访拜访他?”
“那不过只是偶然巧遇,一面之交而已。”孟浩然又想起了在岳阳楼干谒张说的那一幕。
王维道:“张说文韬武略,讲实用,重风骨。玄宗即位后,就是他推荐张九龄为集贤院学士的。”
三杯酒下肚,二人便畅开心扉,无所顾忌地褒贬起当朝的显贵们来。对于那些弄权者,他们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惟独说到张九龄,两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与张子寿大人见过几次面,虽无深交,但一眼便能看出,这是一位耿介儒雅之士,堪称良师益友也。”
“可能是因为政务繁忙,张大人写的诗并不多,但每一首都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气,大有屈子陶潜之精神:‘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一技何足贵,怜是故园春。迟景那能久,芳菲不及新。更愁征戍客,客鬓老边尘。’”孟浩然借着酒兴,吟了一首张九龄的《折杨柳》。
王维道:“读此诗,作者品节自见其间矣。”
孟浩然听了,甚为赞同。
王维又道:“张大人孩童时就极为聪明,七岁就能写出流利的文章。十三岁时上书广州
刺史王方庆,刺史大人读后曰:‘此子必能致远’。果然,他二十多岁就中了进士。”
“可不是么?我有一位朋友,与你同庚,诗作得好极了,时下大凡喜欢吟诵几句诗的人,
几乎都看过他写的诗。”
王维问:“他叫什么名字?”
孟浩然说:“叫李白,号青莲居士。”
王维兴奋起来:“原来你说的是李太白呀!他的大名谁人不知,那个不晓?我特别欣赏
他写的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