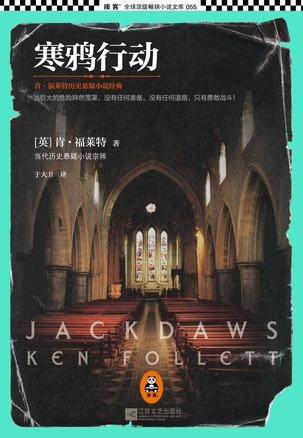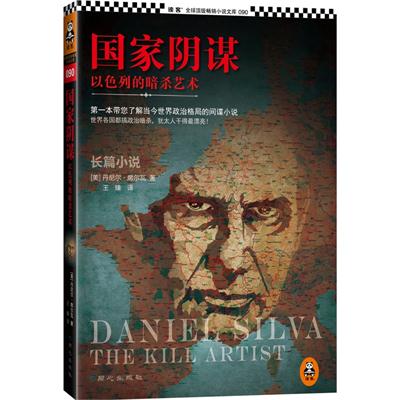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1969年5月初。这年阿弗纳二十二岁,身体健康。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刚刚从精锐部队服役归来。他跟其他人一样,参加过“六日战争”,在预备队中任上尉——在特种部队里服役过的人都是上尉。
“好极了。”他一边上楼洗澡,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两样东西——在大中午洗澡,用英语说“好极了99——代表了阿弗纳的本质。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样更接近他的本质了。部队里有几个人会用一只橘黄色板条箱、几根绳子和一只破水桶做一个移动的澡堂?又有几个人会在其他人的狂笑声中把它用带子捆在坦克上,在沙漠里演习时随时带在身旁?除了澡堂之外,还有一只板条箱,中间切开一个方方正正的洞,这就是内盖夫沙漠上的一个自制的临时厕所。对阿弗纳来说,他不愿意像个猴子一样,蜷缩在沙漠里,让屎壳郎在背上爬来爬去。
并不是这种整洁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碰巧是个爱整洁的人,他并不以此为耻。如果在整个以色列军队中,他是惟一一位在复员时把餐具像四年前发给他的时候那样一尘不染地交回去的,那又怎么样?
毫无疑问,这有点夸张。但即使是夸张,也代表了阿弗纳的本质。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截止到现在为止,阿弗纳还没去过美国。但他的母亲总是说他小时候开口说的第一个字——那是1947年,以色列建国的前一年——不是“妈妈”或者“爸爸”,而是“美国”。这或许有些杜撰的性质,但听起来合情合理,当然听起来也像“阿弗纳”的发音,“阿弗纳”的发音跟“美国”这个词的发音相似。他长大以后,沿着雷霍沃特空旷干裂的大街,赶着看下午场的电影时,美国就成了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成为他的梦想。什么拉娜.特纳,什么约翰·韦恩,什么丽塔·黑沃斯,都是他梦想中的人物。
正是从这些电影中,阿弗纳学会了第一批英语单词——或者更确切地说,美语——像许多以色列人一样,这是一种他自己的语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一直使用的语言,尽管并不十分精确。电影中的美语跟学校里学的英语不一样,是你可以品尝和触摸的东西。你可以将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好了,先生,这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阿弗纳现在再也不可能过多地考虑这些事情了,一个年轻人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时,谁会浪费时间去操心孩提时代的梦想呢?现在他离开了部队。当时他们请他留下来,求他留下来,哄他留下来。但是他不留。四年已经够了。但是,现在呢?是要这个活还是要玛丽·肖莎娜还是去上大学?
阿弗纳洗完澡出来,身上凉爽干净,皮肤黝黑,他朝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用毛巾把自己裹起来。他长得像他父亲——虽然并不是一模一样。父亲的块头比他的大,头发颜色也比他的深,尽管父亲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而且使他变得难以置信的衰老。现在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肌肉也变成了脂肪,他的精神——唉,也时好时坏。父亲一定与浴室凳子上的那个棕色信封有关,虽然不是直接关系。阿弗纳相信这一点,父亲绝不会跟他们谈这个的。相反,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阻止他们。“我的儿子,”他会对他们说,“不能重蹈我的覆辙。”
然而,阿弗纳甚至不会把那封信的事告诉他。他自己会对他们说不的,正如一两个月前他不得不对阿曼的那些人说不一样。“如果你不愿意在部队里做一名现役军人,那好吧。”他们对他说,“那军情局怎么样?”“不去。不去,谢谢。”
他会对莫舍或者棕色信封里的任何人说不。不过,他会去见那个人。星期一总是要去特拉维夫的,因为要接肖莎娜。为什么不去见见他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听一听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两个月来,阿弗纳一直在向以色列航空公司求职。所有的人都说进不去。但是他通过他的一个姑妈把资料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航空公司总部工作。当然,做飞行员是没指望的。他的各项科学测验都没有通过。而且,飞行员都是空军。但是,为以色列航空公司干活也是在为一家航空公司干活。即使做一名乘务员或者在办公室工作也行。也许还有机会旅行,或者短时间离开以色列,去看一眼远方奇妙的世界呢。或者,谁知道呢?也许能遇到一两个训练时认识的、后来当了空军的老朋友呢!他们也许已经当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了,也许有一天还会让阿弗纳试一下着陆,或者至少试一下起飞呢。
阿弗纳坐在马桶盖上,做了一个波音707顺利着陆的姿势。这是加油器。喷气机的巨轮像两片羽毛飘浮在跑道上。这也难怪,自从十岁开始,他就一直在浴室里练习飞机着陆。阿弗纳把波音飞机滑进棚里之后,开始刷牙、穿衣。母亲出去看什么人了。肖莎娜在特拉维夫。父亲——嗯,阿弗纳想,他可以乘公共汽车从雷霍沃特到他父亲家里,到父亲家里之后也许还能借一下他那辆破旧的“雪铁龙”呢。他身上有足够的钱坐公共汽车。在星期六的以色列,钱没有多大用处。就娱乐而言,这个国家封锁得比鼓还要紧,除非你想去餐馆里吃冰冷的三明治。
但在星期一,有“雪铁龙”还是不错的,尽管它在中东是一种最老式的车子。用车去接肖莎娜可以让他们不用搭乘别人的便车,虽然她并不是特别在意。肖莎娜身材苗条,面庞白皙,头发呈蜜黄色,拥有一副埃及人石刻般瘦削的贵族式的容貌,看起来像王族。而骨子里,她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她意志坚强,也没什么因溺爱养成的坏习惯。阿弗纳第一次去她父母家时,用错了一个词,那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在他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家认识,他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她的小表弟给他开了门。
“你是?”
“呃,呃……公主在家吗?”
除了她的外貌之外,用这个词来描述肖莎娜并不合适。公主?那个小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差点把门砰地关上了。幸运的是,肖莎娜这时正好从楼上下来,阿弗纳才没有碰一鼻子灰。
她盼着他会带她去看一场电影呢,但他却不得不在当天晚上回到部队里。他刚刚入伍,不想一开始就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管她公主不公主呢。
“你今晚必须回去吗?”她问他。“其他的人星期天才回去。”
“在我的部队里,今晚就得回去。”
“那好吧,我们散散步吧。”
就这样,他们去散步。那时她还不满十八岁,但是她已经非常清楚,别再问他什么问题了。在以色列,谈到部队里的事情时,人们不再往下问。肖莎娜当然也不问。以后也一次没问。
从他们第一次约会开始,只要他有一两天假期,他们就这样,平均每个月散一次步,看一场电影。假定一年十次,四年就是四十次。二十次散步,二十场电影。星期五搭便车回到雷霍沃特的母亲家中时,一般是在晚上十一点或者午夜。“喂,妈,我回来了。”把乌兹冲锋枪朝墙边一靠,把衣服一挂,倒头就睡。
但是,现在差不多三年过去了,要考虑未来了。有一条路比较简单,而且在他的大多数朋友看来,这条路似乎比较自然。这条路正好在阿弗纳现在站立的这个酷热难当、尘土飞扬的拐角处。他在这个拐角处等那趟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肖莎娜的叔叔准备给他们借些钱,在这里的一块空地上建一栋房子。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阿弗纳和肖莎娜的友谊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或者说,二十次散步和二十场电影的考验。她很快就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书。至于他嘛,他至少有在部队服役的背景。许多幸福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不那么光明的前途之上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背上“法兰克福”这个负担。法兰克福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
法兰克福是阿弗纳一个人的负担。肖莎娜是个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四代都是以色列人。虽然她也有欧洲的背景,但是这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二十一年来,她从来没有闻到过神秘、幽暗、仙境般的森林在两天雨水的浇灌之后散发出来的浓烈的香味。对她来说,雪只是个单词而已。也许只有少数几个幸运的孩子才能在特别寒冷的冬天在耶路撒冷的山上见到那么几个小时。但是她从来没有见到过,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座超过二十年历史的城镇。当然,这座城镇实际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她跟阿弗纳不一样。
1959年,也就是阿弗纳刚刚十二岁时发生的事情,让他既高兴又不安。这种感觉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它非常真实,比电影巨星约翰·韦恩给他的感觉还要强烈。不能把这种感觉当作一个纯粹的幻想。这种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也许他的父母决定带着他和他的弟弟贝尔去看望住在法兰克福的外公时,也没有料到这一点。
阿弗纳来自欧洲又怎么样呢?他是个以色列人,一个中东的孩子,第一批从地球的四个角落聚集在这里的流浪汉的宝贵成果。为什么他不能待在巴勒斯坦的家里?尽管他的父母还怀有一点点乡愁,对中东的情趣和口味还有一些不适应,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还有一些稍纵即逝的记忆,但为什么阿弗纳也会有这些感觉呢?确实,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这些感觉。然而,事实证明,阿弗纳与众不同。
这次度假跟其他假期没什么区别。它是专门为阿弗纳安排的,虽然开始的时候他是最没兴趣的。美国是一回事,可是德国根本唤不起他的任何想象。恰恰相反,德国是一个纳粹分子老是屠杀犹太人的地方,难道不是吗?可是现在,为什么阿弗纳连见都没有见过的外公要他们去那里?
然而,让他感到吃惊的是,1959年的夏天,阿弗纳发现生活中他喜爱的一切——包括他从没见过的不知道自己会喜欢的那些东西——仿佛由一个魔术师汇集在了一个城市,展现在他面前,让他吃惊不已。后来,他回到以色列以后,想把法兰克福描述给他的一些朋友听,可是描述不出来。它是一个梦,一个奇迹,不可言传。
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就想象一座比特拉维夫大得多的城市吧。在这座城市里,一切整洁有序,大街上没有摩肩接踵的人群。而且一切都高高大大,忙忙碌碌,街上有最亮的霓虹灯和无数的汽车。阿弗纳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汽车,跟美国差不多。没有半途而废的楼房,没有成堆的砖块,没有一堆堆的泥巴,没有上面搁着木板的排水沟。
他们刚在法兰克福待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外公给了阿弗纳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并不是阿弗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他记得自己曾在一本美国杂志上见过它的照片,而是外公把这个东西递给他时就像递个苹果一样。这给他一种全新的感受。在以色列,只有总理本·古里安才能收到这样的礼物!
然而,法兰克福奇迹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空气”。
多少年后阿弗纳仍然用这个词来描述它。不是“气候”,而是“空气”。阿弗纳喜欢的气候还是以色列的——阳光、蓝天。即使他在部队里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