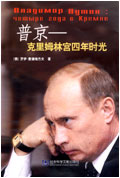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苏联境内并没有“高山俱乐部”——还有一个把重要人物从杜尚别的两个机场带
出来的直升飞机升降地。有十六座建筑。一座用作公寓,虽然是典型的俄国公寓建
筑,六个月以前才修好,其时髦和吸引人的程度犹如一只水泥空心砖,但是从那里
看到的景色一定是很奇妙的。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住在里面。在该地
看见这样一个建筑似乎非常奇怪,但这房子发出的信息是:住在这儿的人都是有特
权的。他们是技术精良的工程人员和专家学者,国家要照顾他们和满足他们的需药。
食物从新开的山路用卡车运来,或者当气候恶劣时空运进去。另一座楼是剧院。再
一座楼是个医院。电视节目由卫星地面站转播,旁边的—座房子里有一些商店。这
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苏联是很不一般的,它只限于党的高级官员和在重要防御工程
中工作的人们。这儿并不是一个滑雪胜地。 从那环形栅栏和警卫岗楼,也能清
楚地看出问题。这两样东西都是最近才有的。识别俄国军事综合设施的标志之一就
是岗楼。伊凡对这些东西有真正的固恋心理。三道栅栏之间,围着两层十米宽的空
地。外层空地上埋着地雷,里层有军犬巡逻。岗楼设在最里边一环上,每个相距二
百米。守岗楼的土兵住在水平中上、水泥浇制的新兵营里……。
“你能把一个卫兵放大吗?”杰克问道。
格雷厄姆对电话说了几句,画面就改变了。一个技术人员已按瑞安的要求行事,
这也是对镜头校准性能和周围大气条件的一次测验。
当镜头拉近时,一个移动着的小点变成了一个人形,穿着厚大衣,可能还戴着
皮毛帽子。他正在让一条看不清品种的大狗散步,右肩上背着一支喀拉什尼科夫式
冲锋枪。人和狗呼气时都喷出白雾。瑞安不自觉地倾身向前,好象这样可以看得清
楚一点似的。
“你看这家伙的肩章是不是绿色的?”他问格雷厄姆。
这个侦察专家咕哝地说道:“是,他是克格勃,没错儿。”
“靠阿富汗那么近?”海军上将若有所思,“他们知道我们有人在那边活动。
我敢断定,他们会认真采取安全措施的。”
“他们真的是需要这些山顶。”瑞安讲他的看法,“七十英里外有几百万人,
他们认为杀死俄国人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地方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这不只是
一个新的设施,有这样的安全措施是不可能的。如果这只是个新设施,他们没有必
要把它设在这里,他们绝对***不会挑选这个地方,既必须修建一座新发电站,
而又冒险暴露给敌方。它现在也许是一个研制机构,但是他们搞这个一定有更大的
图谋。”
“什么样的图谋?”
“可能是对我的卫星打主意。”阿尔特。 格雷厄姆把卫星看成是他自己的。
“他们最近搔扰它们没有?”杰克问道。
“没有,自从去年四月我们严厉地警告他们之后就没有了。这次总算是常识占
了上风。”
那是一个老故事了。前几年里,美国的侦察和早期预警卫星多次被“搔痒”—
—激光或微波能照射在卫星上,虽然不会严重损坏它们,却使它的接收器暂时失灵。
俄国人为什么那样干?那正是个问题。只是为了试一试我们的反应,看看是不是会
引起北美空间防御司令部(NORAD,在科罗拉多州的夏延山) 的一次骚乱?只是为了
他们能判定卫星的敏感程度如何?只是一次示威和警告,说明他们有能力摧毁卫星?
还是仅仅象杰克的英国朋友们所说的生性残忍?很难说苏联人是怎么想的。
当然,他们总是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当一个美国卫星在萨雷沙甘上空被弄得暂
时失去识别能力的时候,他们说是一个天然气输气管道线失火了。事实上,这条在
附近的奇姆肯特——帕夫洛达管道线运送的主要是石油。西方报界被骗过去了。
现在卫星己过境完毕。在隔望屋子里,一大批录相带正在回绕,好了,全部录
相情况可以从容地再细细观察了。
“请让我们再看看‘莫扎特’,还有‘巴赫’也看看。”格里尔下命令。
“***,来来往往的人还真多。”杰克指出。“莫扎特”的住宅区和厂区离
邻近山顶上“巴赫”的阵地只有一公里的样子,但是那道路看来很不好走。图象停
在“巴赫”上,栅栏和岗楼的分布程式又重复了一遍,这次看到环形栅栏的最外层
和第二层之间相距至少二百米。这里的地表是光秃的岩石。杰克怀疑在那里怎样能
埋下地雷——他寻思,或许他们根本没有埋什么雷。地面显然经过爆破和推土机平
整过,象台球桌面一样的一块平地。从岗楼上看,它一定象一个打靶场。
“不会是骗人吧,他们会吗?”格雷厄姆轻声地说。
“那就是他们保卫着的……”瑞安说。
栅栏后面有十三个建筑。在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地面上( 也是经过平整的) ,
有分为两组的十个洞。一组有六个洞,排列为六边形,每个洞直径约三十英尺。第
二组四个洞排列成一个菱形图案,洞口略小,约为二十五英尺。每个洞里有一根直
径约为十五英尺的水泥柱子,立在岩基上,每个洞至少有四十英尺深——当然在屏
幕的图象上你看不出来。每根柱子的顶端有一个金属半球体,看起来是由新月形的
扇形体组成的。
“它们可以打开。我真想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格雷厄姆这样问,也不要谁
回答他。在兰利有二百多人知道社尚别,人人都想知道那些金属圆顶下面是什么东
西。它们是几个月前才安装起来的。
“上将,”杰克说,“我需要敲开另一个保密部门的大门。”
“哪—个?”
“‘茶叶快船’。”
“你别要求得太多!”格里尔用鼻子嗞了一声,“连我还没有获准过问它呢。”
瑞安仰身靠在椅背上。“上将,他们在杜尚别干的跟我们用‘茶叶快船’干的
是否一回事,我们得把它弄清楚。该死的,要是不告诉我们这些地方象什么样子,
又怎么能指望我们知道看到的是些什么东东呢!”
“这话我已经说了好久了。”情报局副局长嘻嘻地笑起来,“战略防御计划机
构不愿意。那么法官(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前法官——译者)不得不找总统去交涉了。”
“那就让他去找总统吧。要是这里的活动跟他们最近提出的武器建议有关,那
又怎么办呢?”
“你认为是这样吗7 ”
“谁改肯定呢?”杰克问,“这是一个巧合。我放心不下。”
“那好。我去同局长谈谈。”
两小时后,瑞安开车回家。他开着他的“美洲虎”XJS 出来,来到乔治·华盛
顿公园路。这是他去英国出差许多快乐回忆中的一个。他十分喜欢这十二汽缸引擎
开起来的那种丝绸一样的轻柔感,以致把他那年高德劭的老“免”(西德大众汽车
公司的一种车型,比较小型省油——译者)置于半退休状态。瑞安把华盛顿的公事
放在—边,这是他—直所向往的。他一连气把车挂到五档,集中精力驱车前进。
“有什么事,詹姆斯?”中央情报局局长问道。
“瑞安认为在‘巴赫’和‘莫扎特’的新行动可能与武器谈判的形势有关。他
可能是正确的。他要深入‘茶叶快船’。我说您得去找总统。”海军上将格里尔笑
了。
“好吧,我给他一个书面证明,无论如何,这总会让帕克斯将军高兴一点。他
们本周末安排了一次全面测试。我替杰克联系去参观。”穆尔法官面带睡意地微笑
着,“您以为如何?”
“我认为他的看法对头,杜尚别和’茶叶快船’实际上是同一个项目。有许多
粗略的相似之处,多得不能认为这只是巧合。咱们的估计得升级了。”
“对。”穆尔转过脸去看窗外。世界又要发生变化了。可能还得过十年或者更
多的时间,但它是要变了。穆尔心里对自己说。从现在算起十年后不会是我的问题
了。但一定是瑞安的问题。“我让他明天就飞到那里去。可能我们在杜尚别问题上
会走好运。弗利给红衣主教带话去了,说我们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
“红衣主教?好的。”
“但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格里尔点点头,“我主耶稣,我希望他能小心谨慎。副局长说道。
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费利托夫上校用左手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自从德米
特里·费多罗维奇逝世以来,国防部已经大不相同了。他是—个早起者,坐在—张
有百年历史的橡木书桌旁边,那是他的妻子在去世以前不久给他买的。差不多——
多少?三十年了,米沙告诉自己。这即将到来的二月,就整整三十年了,他把眼睛
闭了一会儿。三千年了。
他没有哪一天不怀念他的叶莲娜。她的照片摆在这张书桌上,深棕色的图象已
因年久变淡,银镜框已经发乌。他似乎从来没有时间去擦一擦它,也不愿有个女佣
人来打搅自己。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纺锤似的双腿,两臂高高举过头顶,头歪
向一边。那圆圆的、斯拉夫型的脸蛋上展示出一副宽大的、诱人的微笑,完全表达
了她在基洛夫剧团跳舞时所感到的快乐心情。
米沙回忆起看芭蕾舞的第一印象时微笑了一下,一个年轻的装甲兵军官,因为
坦克保养得最好,师部给了一张票去看演出作为奖励。他的印象是:他们怎么能做
到那样?好象踩高跷一样“站在”脚趾尖上。他想起小时候走高跷的样子,可是没
有人家做得这么优美!而且她还向这位坐在前排的漂亮年轻军官微笑呢。那短短的
一瞬间啊!他想,在短短的一眨眼间,他们的眼睛已经心神交接了。她的微笑马上
又变得非常轻淡。她不再为观众微笑,因为在那一刹那间,她是专为他而微笑的。
一颗子弹穿进心脏也没有比它更大的摧毁力量。米沙记不清后来表演的是什么了—
—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那是一出什么芭蕾舞剧。他只记得在后来的一段演出中他
坐在那儿辗转不安,心里翻江倒海,想的只是下一步怎么办。费利托夫中尉已经被
认定是一个有前途的人物、一个优秀的年轻坦克军官,斯大林残暴地清洗军官层,
对他来说意味着好运来临和迅速升迁。他写坦克战术的文章,实行有革新精神的野
战训练,大嚷大叫地发表议论反对西班牙的错误“教训”,以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
那种人的自信心评论一切。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他问自己。红军可不曾教过他怎样去接近一个艺术家。
她不是那种农村女孩子,她对集体农庄工作厌烦已极,愿意委身给任何人——特别
是一个青年红军军官,他完全可以把她从这里带走。米沙至今还记得年轻时候那些
丢人的事( 当时并不认为丢人) :他曾经利用他那军官的肩章跟任何他看上的女孩
子睡觉。
可是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他对自己说。我可怎么办?自然,他处理这事跟
一次军事训练一样。节目一演完,他就打冲锋似的